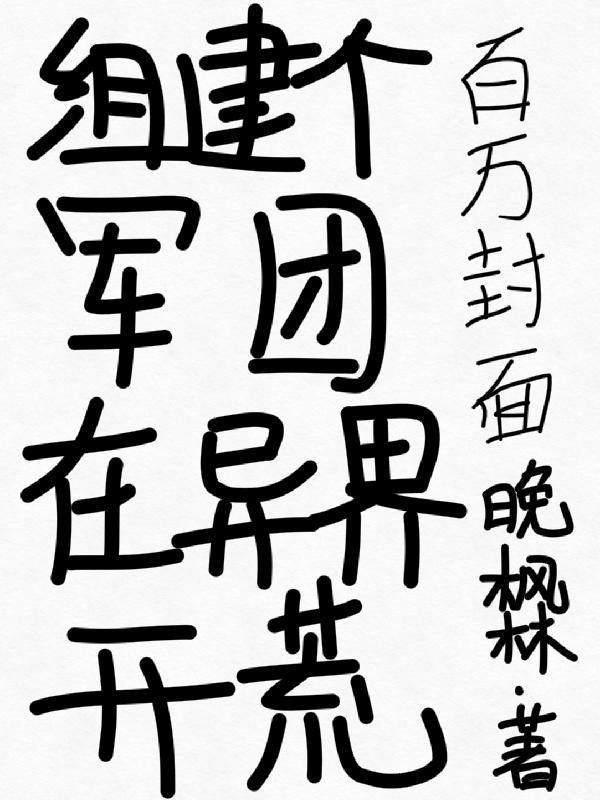言情小说>玄鉴仙族 > 第八百九十八章 术与意(第4页)
第八百九十八章 术与意(第4页)
正是大鸺葵观大真人——娄行。
正逢秋意深浓时,落叶飘零,剑修一言不,在桌旁坐下了,中年人也未开口,默默抬了壶倾酒。
“这么多年不见,道友的剑道越精深了。”
娄行却不答他,那双饱满锋利的眉骨之下双眼熠熠生辉,淡淡地道:
“见薛道友这副模样,是补全了性命,不是第一世了罢。”
眼前这人正是落霞山的大真人薛殃,一身神通圆满,又如静水流深,并不外露,听了对方的话,一杯饮罢,凤眼微阖,起身道:
“不错,两百多年前我五法大成,便补全性命,专研妙术,本就有了冲击虹霞余位的机会…”
“可拜见了师尊,受他考较,终究是道行太浅,未必能配上位子,便着我洗去神通,转世投胎,好些年才寻回来,重炼五法,轻车熟路到了如今的位子。”
娄行静静听罢,双目注视着他,淡淡地道:
“上宗还是体贴自己人…我依稀记得当年我为鸺葵道子,师尊谈了些玩笑话,洋洋洒洒,可惜我愚钝,只记得最后几句。”
薛殃不应他,只平静地往自己的杯里倒酒,娄行却站起身来,面上带笑,饮了酒下肚,更是直言道:
“他说,昔年的书上写的是【宝相空涂膏沃地,庚元亦敢窃金功】,已经是嗟叹不已,我看如今不对了,后人应写:【玄渠不许青羊渡,又使君王奉武修】。”
听了这话,薛殃放了杯,上前一步,摇头道:
“大可不必!”
两人的气氛徒然紧张起来,这位落霞山的大真人眉心紧锁,盯着娄行真人看,对面的剑修分毫不让,直视着他的面孔,冷声道:
“天下之众,自北从南,皆如鱼肉,阿谀奉承,席地而拜,龙鸾潜藏,诸相奉命,莫敢不从!威如魏帝,牧死田亩之间,贵如梁王,溺毙江淮之上!至于齐赵,竟为他人之玩妾,还不够么!”
“堂堂天武之仙裔,骤乎族灭,煌煌中夏之威仪,奉送蛮夷,合天殷州远,于是一山定海中,北海青崖长,便着五门困围守…”
“这天下…还有你等动不得的地方?!”
娄行神色冷峻,与面前的大真人对视,声音低沉,甚至有些咬牙切齿:
“还不够么?要到了什么地步才够?!”
“你…”
薛殃静静地看着他,似乎对他的话语没有太多的感触,一手按着玉杯,轻声道:
“江南的骨节,李江群这一代已经用尽了,等你娄行也走了,江南岂有一人称得上太阳传人?你觉得我落霞不留情,有时…是你等太执着了,天下之变乃是天下人的选择,至于果位变动,争先求证,也是仙道的必然,岂有指责的道理?”
“李江群的事不必提!”
娄行甩了袖子,转过身去,背对着他,冷声道:
“我虽然与他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可他也是个真君子,可如今也是算明白了,余下一个紫霂,不知是他不沾红尘,还是为了显得你们仁慈。”
薛殃终于叹了口气,腰间的六枚短剑微微晃动,道:
“不沾红尘才是仙道。”
娄行真人身上的黑白衣袍无风自动,腰间的葫芦也嗡嗡作响,手中从无到有,慢慢虚空持出一把剑来。
此剑色彩银白,不沾半点外界光色,犹如新铸,二尺九寸三分,短柄握在这剑仙手里,所有的色彩中只有一点朱红醒目,正正点在这剑的脊上。
于是狂风呼啸,飞沙走石,秋风簌簌,薛殃腰上的六把短剑同时消失,磅礴的六道彩光冲天而起,在他身后汇聚,皆长三尺,尾部对齐,尖刃朝外,如同屏风般浮在他身后。
这落霞山的大真人语气终于多了几分复杂:
“昔年把酒言欢,却不想你死在我手上。”
面前这剑仙却仿佛什么也没听到,将那枚葫芦摘下来,轻轻往石桌上一放,便听一声清响,如同翡翠玉珠碰撞,悦耳动听。
这一声未落,便见六道彩色光柱冲天而起,将在天空中呼啸的秋风通通冲散,直入云霄,飞入暗凄凄不见天日的夜色之中,留下六道彩色的尾焰,在天空中灵动地甩动着。
它们在夜空中如同六条彩羽飞龙,扰得天空中的云雾滚滚,又见雷声轰轰作响,转瞬之间这六道庞然大物已经续满了威势,正从高天之上坠下。
薛殃悬浮在夜空之中,脑后彩光重重,晕染开来,一双眼睛明亮如星,玄奥如神明,朱唇微启,一声厚重威严的震动之音在天地之中扩散开来:
“必不小看你!”
地面上的娄行抬起头来,头顶上黑云滚滚,六道彩锋正在往此处汇聚,他望着在瞳孔中放大的色彩,一只手始终按在剑柄上。
“锵!”
一片白光从地界上汹涌而起,荡漾开来,青石也好、残阵也罢,所有断壁残垣齐齐破灭,化为无穷的灰风吹荡开来,太虚中同时响应,出刺耳的铿锵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