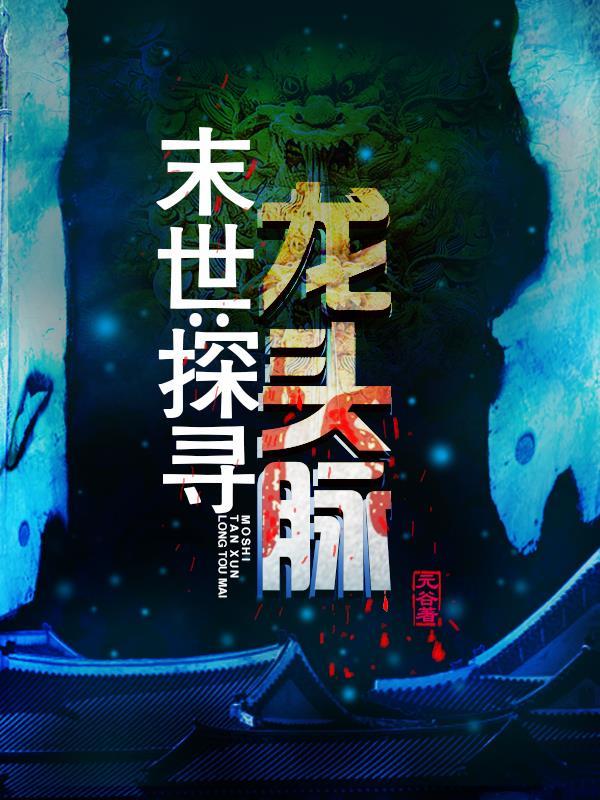言情小说>哪里的孟婆最多 > 第5章 功高盖主不论是非曲直(第2页)
第5章 功高盖主不论是非曲直(第2页)
“太子殿下,慎言。”
太子甩袖坐下,愤愤地掷下杯子,“哼!”
大约过了半月余,娄振康复,只是身体不似往日,愈像一个书生,喜欢的木工也做不了多久,便就此搁置。
“你越来越像一个书生了。”太子看着窗棂下坐着的娄振。
娄振起身,依数行礼,“太子殿下。”
“无妨,今日太傅布下的功课你觉之如何?”
“娄振学识浅薄,不知。”
太子拿起桌上的书卷,“难怪不知。。。。。。”
太子实在憋不住,“你幼时喜欢就罢了,现在这般,是打算跟着你祖父反着干吗?”
娄振接过《鲁班经》,“也是经世致用的书,看看也无妨,咳咳。。。。。。”
“近来许多人都被贬黜了。”
“知道。”
“父皇念太傅辛劳,又嘉奖他了。”
“皇帝仁心,祖父近些日子身体不适,恐要解甲归田了。”
“哦~是吗?”
“是。”
太子看着娄振一如既往的淡泊,“还记得那条白唇竹叶青吗?”
“记得。”
“罢了,你说说,如果你不是在娄家,你还会喜欢木工吗?”
“喜欢。”
“为何?”
“初心如此,至死不悔。”
太子看着娄振橱中尚未做好的木船,实在是简陋,不由轻笑,“你倒是固执,果然是个小老头。”便转身长笑走出了娄府,翻身出了娄府。
娄振在其后行了一个长礼,一阵风吹过,桌上的纸条飘落。
“元泰十九年六月十一日,太傅娄尚于十年间,大肆收取贿赂,买官弼爵。又因结党营私,勾结西南蛮夷,烧毁西南粮草,致使西南九郡沦陷。论罪当诛九族!
——西南俞武侯谏”
元浀朝的三代皇嗣都是独苗苗,故而当初打天下时,封了西南十二郡、东北三郡、藏地等异姓王,手上都握大大小小的权力。
元浀朝重文抑武,而西南俞武侯乃一武将,前朝时追随先帝征战北疆,保元浀朝百姓不受北夷侵扰,因功勋显着,受封西南。
如今皇帝所掌兵权空虚,而为的文臣——娄尚。
“便成了第一只羊羔。”卿铃言及此,捻起一块糕点,细细品尝。
孟锦绯咽下口中糕点,喝下一杯茶,“那娄振得了太子书信,可是带着娄家全族逃了?”
“哪里逃得成?不过都是徒劳。”卿铃执起茶,细细嘬了几口。
“可还记得那只翠鸟。”
“难不成?”
皇帝也不喜文臣夺权,早年间就看出俞武侯的野心,便借着俞武侯呈上的那只翠鸟,警示娄尚。
娄尚这人早已乱了心,那信上所言,虽说有些杜撰,但也并非虚事。
“这是娄振所要经的劫数,本来,那蛇该是咬了那少年帝子,阴差阳错地娄振给受了,那帝子便是承了娄振的情。”
“那娄振也未有阎蜜大人所说的自轻自贱啊?”
“哈哈哈,你见他除了那木工,有什么痴求的吗?”
孟锦绯摇头,迟疑道:“没有。”
钰鹳思绪一番,“师父所言是指,若是娄振带着家人离去,恐一辈子待在一处深山老林,再不复出,而这与他命格扶持新帝恰恰不合。”
“是啊,这就是命运的造化弄人呐。”卿铃轻叹。
“那师父,你们是去把他的族人都杀了吗?”孟锦绯有些惊疑。
卿铃好气地敲了孟锦绯脑门,“我们死物管他们生物作甚,自有人做了呗。”
“那师父你是干啥去了?”
“咳咳。。。。。。这不~要让一个落魄子弟奋起!得去送点金手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