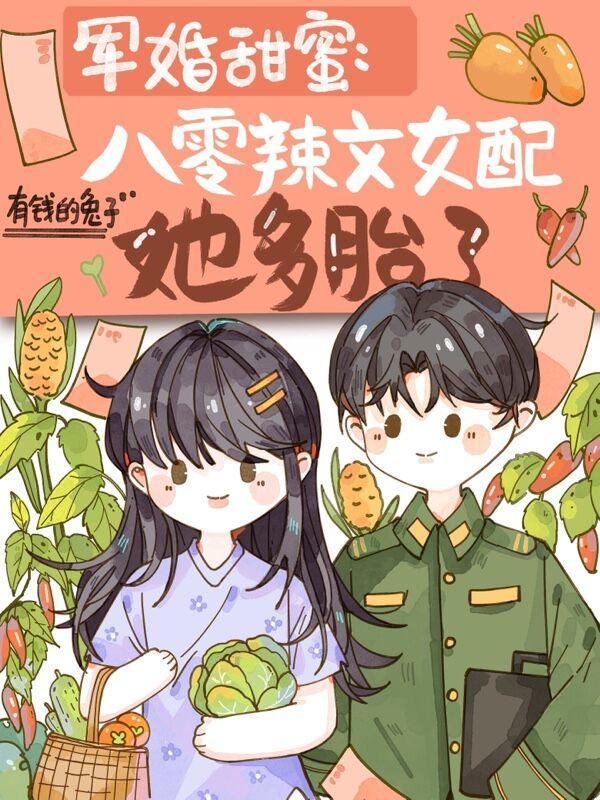言情小说>御兽谱 > 第573章 弄巧反成拙 空叹悔当初(第2页)
第573章 弄巧反成拙 空叹悔当初(第2页)
话毕,平江门猛地站起,呆望着善君,嘴唇颤抖:“你竟也知晓这诗?”
这诗是平江门与采荷女情定终生时所作,赠予了她。
善君黯然神伤地点头,接着道:“起初我很不明白,为何胸前荷花花瓣是十二朵,直到娘亲临终前才告知我,‘既然要而不得情难舍,爱而不见泪未干’,不妨再添一份相思。所以,娘亲为我刺青时,应是这个想法。”
“你胡说八道!”平江苡怒冲冠,冲到善君面前,扬手就要打。
“住手。”平江门颤抖着手臂,厉声喝止。
平江远眼疾手快,瞬间挡在善君身前,护住他:“大哥,今日殿内质证,需以事实为据。你如此冲动,莫不是心中有鬼?”
平江苡双眼血红,举起的手掌,终究还是放下了。
是啊,该心慌意乱的是善君才对,不是自己。
平江苡怏怏不乐地回到原位,垂头丧气,不再吭声。
平江门缓缓坐下,神色愈凝重,满脸忧郁。三轮比对下来,善君竟略占上风。
许久,平江门又问:“那灵犀玉佩,究竟怎么回事?”
酱家酱璞真向前一步,将事情来龙去脉又详述一遍。
平江门听完,直视善君:“善君,你确实没玉佩在身,对此,你作何解释?”
善君却毫不在意地大笑起来:“君上,我若说,那块玉佩本不应现世,您可信?”
平江门一愣:“此话怎讲?”
善君涕泗横流:“娘亲离世那日,将玉佩留给我,叮嘱我保管好,说日后凭它可找亲生父亲。可我当时才七岁,为安葬娘亲,我将它抵押给一户人家。那家主人心善,没收玉佩,还帮忙料理后事。我没留玉佩,让它随娘亲长埋地下,陪伴着她……”
“你的意思是,玉佩是被人掘墓窃取?”平江门冷汗直冒,急切问道。
“不错,我偶然得知那户人家知晓了玉佩价值,趁机盗走。我便潜入他们家,用毒药杀了他们,但有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孩童因在外玩耍逃过一劫。后来为逃命,我跟着乞丐到了王城,最后被宫爷爷带进宫中,陪伴二王子。”善君滔滔不绝。
“他所言属实?”平江门问宫腾。
宫腾“扑通”一声跪地,身体颤抖:“回君上,善君的过往,老奴不知,但他确实是老奴带进宫的。当时见他孤苦伶仃,心生怜悯。请君上责罚……”
还没等宫腾说完,平江苡怒火中烧,满脸怒容,先朝宫腾急切质问:“宫爷爷,不是这样的,您怎能帮他!”接着又对善君怒目而视,厉声怒斥:“善君,没想到你如此胆大妄为,冒充王子,倒反天罡,简直不知死活……”
“住口!”平江门怒不可遏,一个箭步冲下台阶,扬手对着平江苡就是“啪啪”两个清脆的耳光。
大殿内顿时鸦雀无声。众人皆惊愕地看着平江门和平江苡,平江苡的脸颊迅红肿起来,眼中满是委屈和难以置信,他嘴唇颤抖,似乎想要辩解,却又在国君平江门的盛怒之下,不敢出声。
平江门气得浑身抖,指着平江苡吼道:“你身为大王子,不思冷静应对,却在这里肆意妄为,成何体统!”他扫过众人,每一个人都感受到那威严下压抑至极的怒火,“今日之事,关乎王室血脉,不容有丝毫差池,若有人妄图混淆视听,休怪孤王无情!”
平江苡眼中闪过一丝愤恨,但很快又低下头去,他深知此时反驳只会让情况更糟。
平江远眉头微皱,看着这一幕,心中暗自思忖,眼神中流露出复杂的神色,不知是对大哥的同情还是对局势的担忧。
善君则是一脸悲戚,哽咽着说:“君上,我从未想过要冒充任何人,我只是想知道自己的身世,若这刺青和玉佩都是巧合,那我也认了,可我实在是无辜的啊。”他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带着一种令人心碎的凄凉。
“玉手指”站在一旁,眉头紧锁,他深知此事棘手。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身份之争,更牵扯到宫廷的权力平衡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他看向金绍璗,两人目光交汇,彼此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无奈。
这时,酱璞真又开口了:“君上,此事疑点重重,不可轻信一方之言。或许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再做调查,比如询问当年知晓大王子病情的其他人,或者寻找那户人家的幸存者。”
平江门微微点头,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传孤王令,即刻派人去查访当年知晓大王子病情之人,务必找到蛛丝马迹。至于那户人家,也要全力搜寻线索,若有生还者,立刻带到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