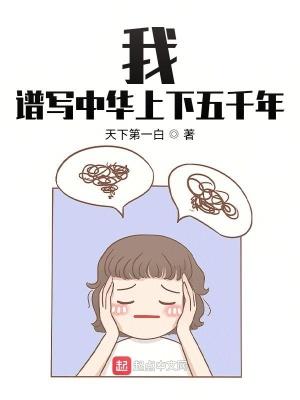言情小说>成为养殖大户后gl > 第43页(第1页)
第43页(第1页)
周纾不得不承认:“是我丢的,只是,祁四郎君怎么会捡它?”
那日她以为祁有望调戏了她,一时气恼才这么做的。如今知道祁有望私藏她的巾帕,她也不觉得生气。
祁有望理直气壮:“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乱扔垃圾,所以帮你处理了。”
说完,她将那条巾帕重掏了出来,道:“我帮你洗干净了,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还给你。刚才擦汗拿错了巾帕,令这方巾帕沾染了我的汗,所以待我再次洗干净后,再还给你吧!”
周纾本不指望将巾帕拿回来了,只是想到祁有望一直藏着她的巾帕,她的心里就感觉怪怪的,有些将自己的贴身之物被人收藏的羞赧感。
而一产生这个念头,周纾便本能地抗拒:只是女子间的手帕之交,她是要成大事的人,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便感到羞涩呢?!
趁着周纾没有生气,祁有望赶紧转移了话题:“小娘子,你想听琴曲吗?”
周纾想听,然而她来这儿的目的不是为了听曲,便克制住了:“这倒是不劳烦祁四郎了,我今日过来是专程答谢祁四郎将那几株茶树照料得很好的。”
祁有望摸了摸后脑勺,有些不好意思:“我也没做什么,只是给他们翻翻土、修剪下枝叶、施肥浇水,没想到才两日,就长出茶叶来了。”
祁有望很坦诚,周纾相信她没必要撒谎,于是这个困扰她的谜题依旧没有答案,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
陈自在到周家的这段日子,也并非日日在茶园中干粗活,他在闲暇之余也曾徜徉各大书铺,并从中结识了几位州学的学生,便相约踏青、参加雅集。
他与他们弹琴、斗茶、品酒,极尽文雅之事。
到了兴头上,他忽然想起一事,便旁敲侧击地问:“冯兄与张兄都是上饶人,自幼便在信州城中长大,相信没什么事是不知的。二位可知祁家四郎君?”
那冯、张二人被他不动声色的吹捧,心中十分畅快,闻言,不假思索地道:“信州城何人不知祁四郎呢?不过那是个纨绔,不值得陈兄关注。”
“纨绔?”陈自在眼神闪了闪。
冯、张二人就像打开了话闸子,道:“祁四郎运气好,投胎投到祁家,上有曾被官家钦点为应天府书院讲授的爹,还有一个宝泉监知监的长兄,他那长兄可了不得,娶的妻子是左谏议大夫……”
从祁家安人到祁有望,二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陈自在却从中抓住了一个细节,问:“你们说他在祁家排行老四,可你们说了他的长兄和二哥,那他那位三哥呢?”
二人本来在兴头上,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听他问及祁三郎,登时便清醒了几分:“祁三郎啊,那可不好说。”
莫说陈自在了,便是另外三位从别县过来求学的学子也好奇得很,忙追问:“祁三郎怎么了?”
冯、张二人环顾四周,然后压低了声音,道:“那祁三郎在祁家是个不受宠的,听说他出生后才几个时辰,他娘就被他克死了,那日祁家喜事变丧事,晦气得很。”
“祁讲授与正妻恩爱得很,若非正妻死了,他也不至于会娶续弦。他那续弦刚好是祁家安人的外甥女,当年才十八岁,就欢天喜地地进了祁家的门,第二年就生了祁四郎。”
“听闻祁四郎出生时,正值寒冬,然而那一日祁家的牛生了双胎,宅中花草树木如枯木逢春,都活过来了,所以祁家安人认为这是祥瑞,对祁四郎疼爱得紧!”
“一个出生便克死了亲娘,一个出生自带祥瑞,可想而知,祁家这老三跟老四在家中的地位有多悬殊了。”
二人又瞧瞧地补充了句:“那祁三郎后来更是搬出了祁家大宅,住进了城西南的别业里。”
陈自在摩挲着指腹,眼神晦涩难明。
雅集结束后,他回了周家。这段时间,有他的姑姑为他撑腰,他出行皆是马车,回来后,周家的仆役都不敢拿轻蔑的眼神看他,他仿佛是生长于此的主人家。
然而,周纾的眼神将他打回了原形,好似在告诉他,周家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他的那颗心顿时就冷了,冷得疼。
堂上姑父的笑声很是刺耳,而那道今日还被人谈及的身影更是刺痛了他那敏感的心。他抿唇冷眼看着,直到他走到他们面前,脸上才释放出笑容来。
“姑父、表妹,我回来啦!”
周员外笑呵呵地看着他:“安哥回来啦,今日的雅集如何?”
“我与他们志相投、相谈甚欢,今日的雅集也算是略有所得。”陈自在说完,将目光投向祁有望,“祁四郎君今日怎么过来了?”
祁有望翘起了唇角,显得很是愉悦:“周小娘子邀我来做客,我就来啦!”
陈自在扯了扯嘴角,也不去招惹她,而是问候了周员外与周纾后,便先回了客院。
他在客院看见了陈见娇,颇为疑惑:“娇娘,你怎么在这里,祁四郎过来了,你不出去见他?”
陈见娇道:“姑母说那是外男,我还未出,不能做那么失礼的事情。”
若非在姑母的眼皮子底下,她不才不会拘泥于这些礼节呢!
陈自在眼中闪过一丝不满,道:“姑母不让你出去,可是表妹却在外头。”
他怀疑姑母是看中了祁有望的家世,想撮合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