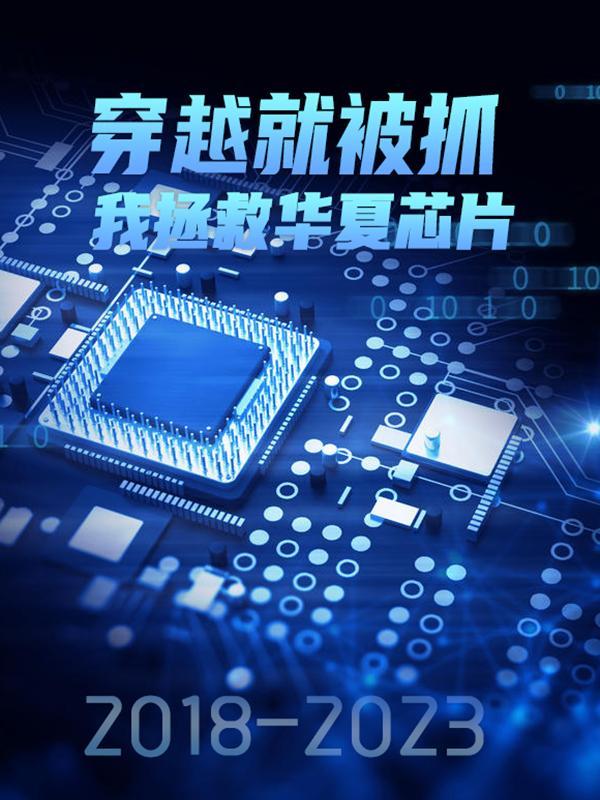言情小说>开局被架空,朕要成就千古一帝 > 第844章 这是好事呐4k字大章(第1页)
第844章 这是好事呐4k字大章(第1页)
坐在茶台边倒茶的濮鸿宝恍然大悟道:“原来东宫是藏着这个心思。”
书桌旁,提笔写完字的楚佑伦轻放下手中的毫笔,似笑非笑道:“且等着吧,东宫与老三之间的较量还不算完呢……”
濮鸿宝沉吟片刻后问道:“那……殿下,咱们是不是该有所行动呢?”
楚佑伦笑着走到濮鸿宝身前,神色轻松地端起杯刚倒好的热茶,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杯中沸腾着热气的茶水,慢吞吞的说道:“老师,这回老三那儿折了个沈嘉枰,你说……靠在他身边的那些个人心里泛不泛哆嗦呢?”
濮鸿宝也不傻,一下便听明白楚佑伦话中蕴藏着的深意了,“殿下是想趁虚而入?”
“不要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楚佑伦喝了口茶,笑呵呵地说道:“我只是让围在老三跟前的臣子们明白识时务者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
“沈嘉枰一死,那些个靠在老三跟前的四五品中层官吏们心里都泛哆嗦呢,如今情势还没到全无退路的绝境,这帮见风便怵,四处摇摆的人是狠不下心来与老三死抱一把的。”
濮鸿宝皱眉道:“可……这也不见得他们会向咱们靠来。”
楚佑伦异常自信地说道:“除了咱们,他们没得选了。”
“啊?”濮鸿宝有些惊讶地张了张嘴,随即问道:“老臣斗胆求问,殿下有何把握让他们死靠向咱们?”
顿了顿,濮鸿宝又说道:“就如殿下所言,现如今靠向三皇子一头的那些个四五品中层官吏们经过这次事后,大多数人心中都有些摇摆,不见得会跟三皇子死抱成团,说不定已然准备转投东宫了,又……又怎会靠向咱们呢?”
“很简单,我让他们不敢去投东宫就是了。”楚佑伦脸上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濮鸿宝被他这话弄得有些不知所措,略微犯懵道:“殿下有何高策,还望直言……”
“沈嘉枰被老三推出来顶雷后是什么下场?”
“悬梁上吊。”
说着,濮鸿宝又道:“可东宫并未追究其家眷,甚至太子还下令要厚葬沈嘉枰。”
“呵,我这大哥厉害就厉害在这,沈嘉枰身为老三麾下的马前卒之一,往年没少找东宫的麻烦,可等他落到我大哥手里后,我大哥却未趁势报复,祸及家人,有这么件事撑名声,谁人不说他这个储君宽仁德厚呐!”
楚佑伦赞叹连连的说完这段话后,忽地话锋一转,语气森然道:“可如果大伙转头现这位太子储君宽仁德厚的形象与其真实本心截然相反,他们心里会不会打颤,会不会犯怵?”
濮鸿宝一愣:“殿下这话是什么意思……”
“沈嘉枰自杀后,他的家眷携带着不少银两回乡了吧?”
“是有这么回事,我还听说,沈嘉枰那二十余口家眷在离京回乡当日,刘阁老刘广义还亲自派管家去相送了,听说还给沈家人拿了不少银子。”
话说到一半,濮鸿宝突地打起寒颤来,犹如触电般瞪大了双眼,好似瞬间明白楚佑伦的打算了……
“殿下,您……”
“可惜了,沈家的这二十多口人,注定是回不到故乡了。”
濮鸿宝心中寒,看向坐在对面这个自己从小看到大的二皇子楚佑伦,忽感到有些陌生。
沉默许久后,濮鸿宝才问道:“二十多人骤然离世,闹出的动静不会小,倘引起东宫的注意怎么办?”
楚佑伦格外轻松地摆手道:“围在老大跟前的那帮人里,恨沈嘉枰入骨的人也不是没有,虽说我在其中起了些作用,但这事就是东宫的人做得,老大……查到了又能如何?”
濮鸿宝心下愕然,一时间,竟不知该佩服楚佑伦行事的缜密,还是该鄙夷他手段的狠绝……
“沈家二十余人归乡途中遭遇屠戮的消息只要传回京师,老三身边那些个摇摆不定的墙头草就不敢再往东宫跟前凑了,给他们的,只会有两个选择,要么跟老三死抱一块,要么……往咱们这边探头。”
楚佑伦眯了眯眼,将手中茶杯轻轻放下后说道:“联络这帮人就用不着老师出面了,我会让尤新知去办的。”
尤新知,为现任光禄寺卿,于明面上,他是无党无派的朝中大员,但实则只有少数人心里清楚,尤新知是隐藏极深的“二皇子党”。
濮鸿宝点了点头,遂又问道:“那老臣有什么要做的吗?”
正当楚佑伦打算回话时,屋外却骤然响起一阵敲门声,“二爷,属下有要事要报。”
楚佑伦驭下极严,他知道,若不是有要紧之事要紧急汇报,府里下人是绝不敢在自己与人商谈正事之际打扰的,于是,他也很干脆地把房门打了开来,看向站在门外来报的壮实青年,询问道:“严典,你怎么回府了?有什么事?”
那被称作严典的壮汉先是观察了下四周,后而抱拳说道:“属下有件要事需禀报殿下。”
顿了顿,他压低声音道:“今早,四殿下被放出府了,陛下有旨,废除了禁足四殿下的惩罚。”
“哦?”楚佑伦微微一愣,旋即看了眼屋内同样惊讶的濮鸿宝,脸上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容,“恩……这是好事呐……”
说着,他挥手示意严典退下,重新合上了房门。
“老师,你接下来还真有件事要替我去办了。”
楚佑伦双手撑桌,眼神变得无比犀利起来。
濮鸿宝一边听他讲述着计划与安排,一边看向书桌上那由楚佑伦亲笔写下的四个字——戒躁耐忍,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