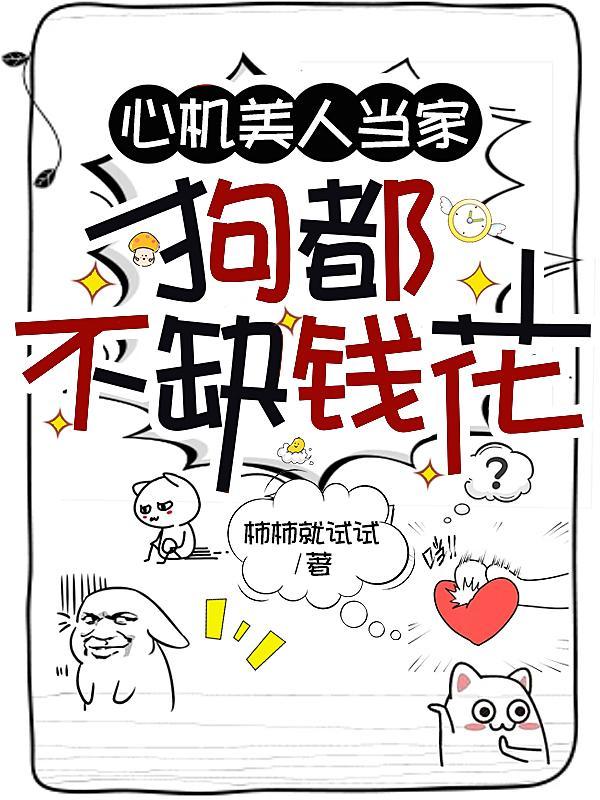言情小说>春日迷情 > 第222章 花边新闻(第1页)
第222章 花边新闻(第1页)
薛砚辞终于打破宁静,他侧头望向窗外,片刻后转头问向舒瑜,声音低沉而沙哑:“我托付你的事,进展如何?”
舒瑜心领神会,那是他们共同守护的秘密。
“一切顺利,经过催眠治疗,她在记忆中已经找不到你的痕迹了。医生说,只要再巩固治疗一两次,就基本可以确定了。”
她轻声回答,言语间夹杂着复杂的感情。
郭以珏握着方向盘,从后视镜中投去一瞥,嘴角挂着一抹苦涩的笑:“你真是‘伟大’,替她承受了一切,同归于尽还不够,还要彻底从她的世界消失,这份牺牲,连菩萨都会汗颜吧。”
对于这番刺耳的讽刺,薛砚辞并未作出任何回应,也未像往常那般反击,只是静静坐着,仿佛外界的一切已与其无关。
舒瑜的眼神在薛砚辞身上流转,充满了疼惜与困惑:“哥,为何不让她知晓你所做的一切牺牲,你明明——”话
未尽,就被薛砚辞打断:“虞冉呢?她最近怎么样了?”
舒瑜叹了口气,回答道:“虞冉现在情况好多了,这一个月来都没有再犯病。”
随后,她带着一丝忧虑,轻声询问:“哥,接下来,是不是该为自己打算一下了?”
这话似乎触动了车内每个人的神经,让空气再次凝固起来。
薛砚辞轻轻摇了摇头,乌黑的丝随着动作在空气中划过一道弧线,语气淡然地道:“我的事儿,你就别往心里搁了。”
辛满一听,眉头微蹙,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这怎么能行?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她虽非法律科班出身,但从得知消息的那一刻起,便马不停蹄地在路上查阅相关法律条款和案例,手机屏幕上的光映照在她认真专注的面庞上,指尖飞快滑动间,已将薛砚辞面临的困境与可能的法律援助方案铭记于心。
邹泽译闻言,嘴角勾起一抹冷嘲,声音里夹杂着不屑:“是吗?你以为杨老师得知了会不忧虑?”
薛砚辞目光一闪,终是打破沉默,对邹泽译低声道:“少说两句。”
邹泽译语调阴阳怪气,故意放大音量:“哟,你还挺在意她的看法啊?我还以为你为了那个女人,连自己的母亲都能抛之脑后了。”
薛砚辞的声音里透着不易察觉的坚决:“我的选择,与她无关。”
未及他提及名字,邹泽译已心知肚明他所指为何,暗自腹诽,嘴上却不再纠缠。
薛砚辞没有多作解释,只沉声嘱咐:“无论如何,别让我妈知道。”
……夜幕降临,公寓里灯火初上,薛砚辞步入浴室,温热的水柱打在疲惫的身躯上,似乎能短暂洗刷掉内心的纠葛。湿漉漉的头来不及吹干,他就匆忙走出,额前碎贴着脸颊,显得格外落拓不羁。
权晔与程应锦适时抵达,三人的眼神交汇,无需多言,一切尽在不言中。
薛砚辞刚落座,程应锦便开门见山:“你和周度早有默契,是吧?从杨老师那次事件就开始布局了?”
薛砚辞沉默以对,嘴角微微上扬,不置可否,却胜似千言万语。
程应锦面色凝重,话语间的肯定毋庸置疑:“之后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让薛家人误解你贪图家产,以此消弭他们的戒心。”
“你始终未向虞冉袒露身份,是因为从没想过要真正拥有她。”
程应锦的话语如锋利的刀刃,直击要害,“你早做好了进去的准备,是这样吧?”
薛砚辞缓缓弯腰,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烟,轻巧地点燃,深吸一口,神色淡定自若,仿佛置身事外,丝毫不见即将身陷囹圄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