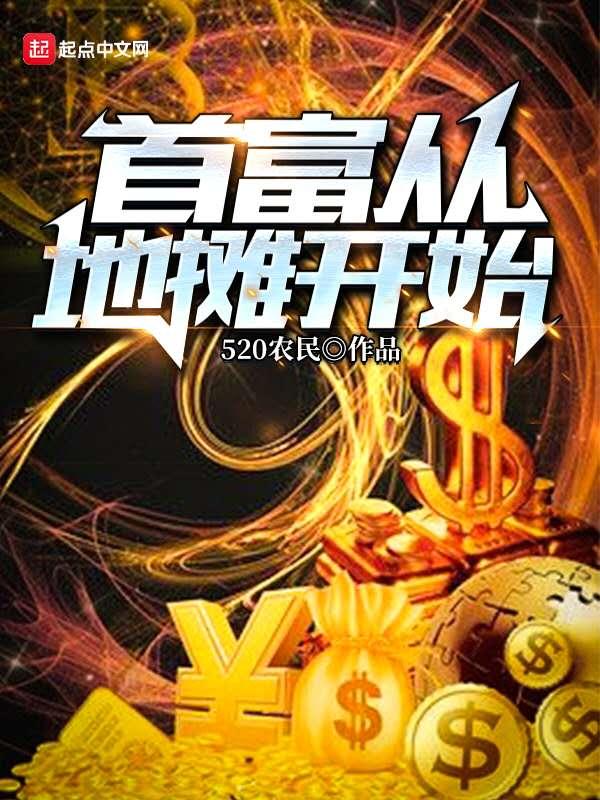言情小说>热血豪情 > 第190章 第182章幡然悔悟(第1页)
第190章 第182章幡然悔悟(第1页)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王憨扑进“锤王”胸怀的刹那间,出手变刀劈了下来,“锤王”的咽喉、前胸被划开,血像喷出的泉水涌出。与此同时,王憨后肩被其剑刺中,臀部也挨了其一戟,以自己受伤的代价而换取了“锤王”一命。
强者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也多亏“快手一刀”王憨胆大心细,胸有成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在其身后“剑雄”、“戟霸”奋力向自己袭击之势,看准了火色,掌握住了火候,就在其器械刚触及身体的刹那间,倏地来个前扑攻向了对面的“锤王”,化解了“剑雄”、“戟霸”的攻势,更把握住其剑、戟入肉深浅,便运用肌肉团负伤的抽搐,在锁住了此剑、戟的同时,倏地来个回身、扭腰,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里,突然出手,用掌力划过身侧,切入了“戟霸”的小腹中。
当“剑雄”用力抽出了刺入王憨后肩的长剑时,他已蓦然现“锤王”喉中喷出的血雨,以及“戟霸”流出蠕动的肠子。这一切是那么的短暂,只在须臾中完成,可见王憨出手之快,“掌刀出手索命,无命空手不回”,真不愧为“快手一刀”。
“剑雄”眨眼之间看二人丧命,惊恐之余凄厉呼叫一声:“二弟、三弟——”余音在绕未断之时,王憨的掌力又像闪电般冲着“剑雄”疾斩而下。“剑雄”急忙举剑招架,可是已晚,就在他的剑才举到一半之时,已感到自己胸腹间有被人撕裂的痛楚,由头顶一下子直传到脚心,于是“二弟、三弟——”的凄厉的吼声倏然而断,因为“剑雄”也已命丧黄泉,再也喊不出来了。
王憨永远都对自己的手充满着信心,他知道无论在多么险象环生的状况下,只要自己的手不断,还能动的情况下,他就有把握维护自己“掌刀出手索命,无命空手不回”的信誉。然而他对自己的脚,却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因为当他想要飞身过去抢救处于“黑白秀士”两柄钢筋铁骨扇下垂危的孙飞霞时,一个踉跄差些跌倒。
当然他一个踉跄险些跌倒的原因,一个是救人心切,也是因后臂入肉达骨的剑伤。这可是他一个严重而要命的失误,因为他的一步之差,这一步的距离无异于生与死的界限,而这一步之差,使孙飞霞走到了别无选择的地步。
孙飞霞望着其两柄钢筋铁骨扇一上一下的横切而至,已知道自己无法躲过这迅猛而凌厉的合击之力,于是在一瞬间,她当机立断,做了个痛苦的选择,来个与其同归于尽,放弃了一边的防守,趁着她一把短剑架住由上而下的“白秀士”的钢筋铁骨扇的同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她倏地将另一把短剑奋力刺入了“黑秀士”的腹中。
当然她的那一剑架不住“白秀士”那钢筋铁骨扇由上而下的重击,随着碎裂的骨骼声响,孙飞霞的髋骨尽碎,一跤跌坐在地上。她知道自己罪有应得,劫数难逃,大限将至,索性闭上了眼,努力克制着自己内心的痛苦,再等着“白秀士”第二次的袭击。
“白秀士”看“黑秀士”死在孙飞霞之手,不由得暴跳如雷,冲着孙飞霞吼叫:“你杀了我兄,拿命过来。。。。。。”说着手执钢筋铁骨扇冰冷的刚刚刺进孙飞霞的颈项,刚要切入喉管,可已再也切不进一分,猛听得“白秀士”像狼般的嗥叫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白秀士”要其孙飞霞的命时,他怎么会出杀猪般的嚎叫呢?因为“快手一刀”王憨的掌力已到,而他执那钢筋铁骨扇的手已断。他惨痛地号叫着挥舞着独臂,看着掉地的那手,受伤的臂滴洒着鲜血,身躯跃起,像鬼一搬越墙而去。识时务者为俊杰,他知道自己决不是“快手一刀”的对手,那怕他亦身受重伤,若不尽快逃走,恐难以脱身。
惨烈的打斗场面业已结束,此时此地又恢复了平静。向晚的深秋有了凉意,夕阳却像鲜血一样的红,以印证着这里已生过一场惨绝人寰的你死我活的争斗。
王憨念及与孙飞霞一往的友情,把她抱在怀中,看着气喘嘘嘘的她,现她的脸色却出奇的惨白,白得那么怕人,没有一丝血色,气息奄奄,日命危急,知道她将已不久人世,虽然她做了许多让人痛心的事,但已对她恨不起来,倒对她产生了怜悯之心。
孙飞霞看着王憨不离不弃的抱着自己,并不以她做了对不起他们的事而产生反感与报复,反而摒弃前嫌,不顾自己的安危伸手救她,实在感动她,想自己做了那些对不起他们的事,也是自己受人挟持无奈之举,便流出了眼泪。那眼泪是出之感激,或是出之忏悔,或是出之悔悟,只有她自己心里知道。
她长叹一声,气若游丝的在王憨的耳边说:“我。。。。。。我已摆脱了那。。。。。。那只看不见的幽灵的手。。。。。。”
王憨痛苦的哽声说:“是。。。。。。是的。”
“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你知道吗?到现在,我才觉我。。。。。。我所爱的人,一直是。。。。。。是你,只是,只是。。。。。。”孙飞霞的声音更是微弱。
王憨怒其不争,颤抖地说:“唉!你。。。。。。你。。。。。。你好傻。。。。。。”
孙飞霞凄然一笑,断断续续地说:“我。。。。。。我知道,你。。。。。。你心里也一直的爱着我。。。。。。然。。。。。。然而造化如此弄。。。。。。弄人,偏偏我。。。。。。我们俩都。。。。。。都认识他弥。。。。。。弥勒吴那。。。。。。那个‘赖皮’。。。。。。替我转告他,他。。。。。。他真是个‘大扫把’,可是他。。。。。。他却也是个可。。。。。。可爱的朋。。。。。。朋友,是我。。。。。。我对不起他。”
王憨的心在滴血,知道她的时日不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只能轻轻的点头,听她说。
“唉!人。。。。。。人不能一步走错,一步错。。。。。。错了,会步步皆。。。。。。皆错。那。。。。。。那个女人叫。。。。。。叫皇甫玉梅是不?待我见到她的时候,我会向她忏悔,我。。。。。。我也会转。。。。。。转告她,你。。。。。。你真是个值。。。。。。值得她爱的人。王憨,有她与我。。。。。。我为伴,我。。。。。。我也好难过,虽然是她夺走了我。。。。。。我的心上人,但我也会告诉她,你对她的怀念。。。。。。”
王憨沙哑地说:“我知道。。。。。。”
“我。。。。。。我还有一个是你。。。。。。你所不知道的秘。。。。。。秘密,那就是我。。。。。。我并不是‘梅花门’的头,真正‘梅花门’的头是另。。。。。。另有其人。。。。。。”
“我知道,大少李彬已疯了,‘梅花门’也将随着他的疯而散了。。。。。。”
“不。。。。。。不,你错了,真正的‘梅花门’之不。。。。。。不是他,是。。。。。。是一个谁也不。。。。。。不知道的人,他就像一个藏头露尾的可怕的神秘的幽灵,谁也不知道他的庐山真面目。我。。。。。。我和大少李彬都。。。。。。都是那。。。。。。那个人的傀儡,唯他马是瞻,听。。。。。。听命于他,因为我。。。。。。我们一直都受到他的药物‘续命救生丸’的控制。。。。。。”
这也在王憨的意料之中,因为他和孙飞霞从小就在一起玩耍,她的性格及才能,他是清楚的,凭她那两下子,她领导不了“梅花门”这诡秘的庞大的组织,其身后定有个可怕的幽灵在行水掌舵,她之不过是个马前卒而已,今从她嘴里说出来,正验证了自己的推测,果不其然,她身后有个神秘可怕的人,为能听清楚她说的话,王憨竖起了耳朵附在了孙飞霞的嘴边。
“‘梅花门’里的人,每。。。。。。每一个都。。。。。。都受到他。。。。。。他的药物控。。。。。。控制,所以他们对我。。。。。。我的叛逆之心大为恐惧,怕受到牵连,他。。。。。。他们才会置。。。。。。置我于死。。。。。。死地。你。。。。。。你一定要找。。。。。。找到这。。。。。。这个神秘人,要。。。。。。要不然,‘梅花门’永远都。。。。。。都会存在,江湖上会永。。。。。。永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