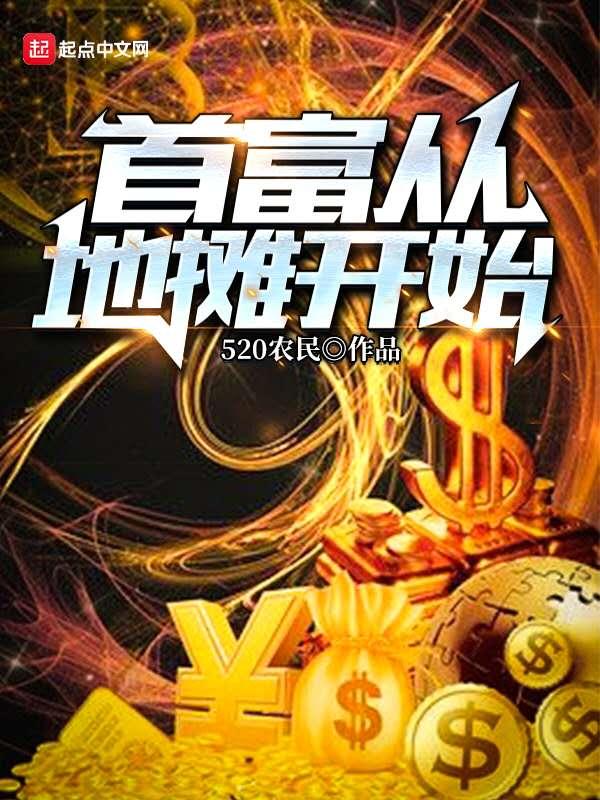言情小说>完蛋!陛下这是要白嫖我! > 第314章(第2页)
第314章(第2页)
林小风走到牢房外面,静静地看着骆文彬。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既有对骆文彬的同情与怜悯,也有对这场战争的无奈与感慨。他转身坐在郭天阳准备好的椅子上,背对着骆文彬问道:“牢里的是骆文彬吗?”
骆文彬闭着眼睛不回答,他仿佛已经对这个世界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与期待。然而,当林小风说出“我们是奉旨来问话的”时,他还是吸了口气坐起来。虽然他反叛了明朝,但听到大明皇帝要问他话还是表示出了尊重。
咦?怎么只看到一个椅背和背影呢?骆文彬心中充满了疑惑与不解。然而,他也知道,此刻的自己已经是一个阶下囚,没有资格去追问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足下是何人?”骆文彬坐在地上,神色平静地问道。他的声音虽然疲惫,但却依然保持着几分威严与尊严。
“我和你一样都是大明的子民。”林小风回答得很沉稳,他的声音仿佛一股暖流,温暖了骆文彬冰冷的心房。
骆文彬身子微微一颤,然后抬起头仔细看了看那个背影。过了一会儿,他摇了摇头,否定了自己之前的猜测。然后他说:“我是大顺的磁侯左营制将军,不是大明的子民!”他的声音中带着几分坚定与执着。
然而,林小风的声音却更加沉稳了:“你生在大明,长在大明,死后也是大明的鬼。中间那段做流贼的经历,根本不值一提。”他的话语仿佛一把锋利的刀,刺破了骆文彬心中的幻想与执着。
骆文彬想反驳,但却被林小风的话打断了:“我们是奉旨来问话的。你为什么要反叛?”他的声音中带着几分严厉与质问。
骆文彬激动地说道:“天灾不断,百姓生活困苦。如果不反,就会饿死或者被那些追税的官吏逼死。如果你处在我的境地,你也会反的!”他的话语中带着几分无奈与悲愤。
然而,林小风却继续追问:“那你反叛后得到了温饱,为什么不投降朝廷,反而继续当流贼呢?”他的声音中带着几分质疑与不解。
骆文彬的心情被搅乱了,他愤怒地说道:“只要那些贪官污吏还在,我们就绝不会投降!而且,天下还有那么多人在挨饿,我们要救他们于水火之中!”他的声音中带着几分坚定与执着,仿佛这是他一生都无法放弃的信念。
然而,林小风却冷笑了一声,他的气场让骆文彬感到了一股寒意。他冷冷地说道:“你刚才的话,自己相信吗?流贼为什么被称为流贼?他们打着均田免粮的旗号,干的却是奸淫掳掠的勾当!”他的话语仿佛一把锋利的刀,刺破了骆文彬心中的幻想与信念。
骆文彬争辩道:“那只是个别人的行为!我们大顺军纪严明,所过之处秋毫无犯!”他的声音中带着几分坚定与自豪,仿佛这是他一生都无法放弃的荣耀。
然而,林小风却哼了一声,然后转移了话题。他知道,骆文彬对大顺还抱有幻想,必须打破这个幻想,让他认清现实。他冷冷地问道:“我们也是奉旨来问话的。你觉得大顺还能撑多久?”他的声音中带着几分质问与嘲讽,仿佛已经看到了大顺的灭亡与衰败。
景常浩虽然读的书不算多,但对大明朝廷里的事情却是了如指掌,仿佛每一道宫廷的阴影都藏着他的智慧。他叹了口气,眼中闪烁着对历史沧桑的洞察:“大明在山东原来有六个藩王的地盘,齐王以前封在青州府,那是一片繁华之地,可惜永乐年间就被废了,如同秋日里的一片落叶,静静地离开了枝头。汉王因为叛乱被杀,他自己还有十二个儿子,都被瞻基皇帝给一锅端了,汉王家从此就绝了后,如同熄灭的烛火,再无复燃之可能。”
“泾王呢,是封在沂州的,那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结果嘉靖皇帝那会儿因为他没儿子,也给废了。仿佛是命运的玩笑,让一个王府的辉煌瞬间化为乌有。”
“德王管着德州,那是个兵家必争之地。结果林小风十二年那场大乱,建奴打过来,德王由枢和他一家老小都被抓走了,像是狂风中的一粒尘埃,被无情地卷走。第二年,才由他弟弟由栎接替了德王的位置,但那份荣耀与尊严,早已不复存在。”
“衡王住在青州,那是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鲁王则是在兖州,两地相隔不远,却仿佛是两个世界。衡王的府邸古朴典雅,鲁王的宫殿则气势恢宏,两者各具特色,都是山东的明珠。”
“皇上啊,要是您想从藩王那儿弄点钱,青州和兖州这两个地方或许可以动动脑筋。”景常浩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仿佛每一个字都蕴含着深思熟虑的智慧。
景常浩心里清楚,自成现在最缺的就是钱,得赶紧找大笔的钱来。自从刘泽清被蒋太微除掉后,他的兵都归了京师,山东这边守军虽然多,但能打的却没几个。这时候打山东,真是天赐良机,仿佛是上天特意为自成准备的一份厚礼。
自成瞅着景常浩,压低声音说:“曲阜虽然没藩王,但那儿有个比藩王还有钱的主儿。”他的眼神中闪烁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光芒,仿佛是对未来的期待与对现实的无奈交织在一起。
景常浩一听,惊讶得瞪大了眼,仿佛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观:“您说的是……孔府?”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仿佛是对这个提议的震惊与不安。
“对头!”自成点了点头,脸色却不怎么好看,仿佛是乌云压顶,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风暴。“这……这可不是好主意啊!孔府是孔子的后代住的地方,读书人眼里那是圣地。咱们要是去抢他们的钱,那就是跟全天下的读书人结仇了。”景常浩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焦虑与担忧,仿佛是在劝说一个即将走上歧途的孩子。
“这……这……”自成也犹豫了,他的眼神中闪烁着一种复杂的情绪,仿佛是在权衡利弊,又仿佛是在寻找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臣斗胆进言,皇上您还是别打这个主意了。”景常浩尽力劝着,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恳求与无奈,仿佛是在为一个即将做出的错误决定而惋惜。
但他心里也明白,真要是去抢孔府,后果可不敢想。那将是一场无法预料的灾难,仿佛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无尽的邪恶与苦难。
郝摇旗和高一功俩人在一旁听着,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们对读书人本来就没啥好感,对孔子的后代就更别提尊敬了。反正是被读书人逼反的,自成说啥他们就干啥。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冷漠与无情,仿佛是对这个世界的嘲讽与不屑。
自成冷笑一声,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决绝与冷酷:“我说啊,咱们可以假装是建奴干的。最近莒州那边不是有建奴的踪迹吗?离曲阜也就四百里地。咱们扮成建奴去曲阜闹事,到时候出了事,那也是建奴的锅,跟咱们大顺可没关系。”他的计划仿佛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等待着无辜者的踏入。
“这……”景常浩还想说什么,但又不知道说啥好。他的心中充满了矛盾与挣扎,仿佛是一个被撕裂的灵魂,在善与恶之间徘徊。
他想了想,还是说:“咱们跟建奴语言不通啊,万一露馅了怎么办?”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担忧与无奈,仿佛是在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苦恼。
“没事!”摇旗一听就来了劲,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兴奋与期待,“建奴里头有汉八旗,说的都是中原话,纯得很。”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自信与得意,仿佛是为这个计划的成功而欢呼。
看景常浩还是犹犹豫豫的,自成就问:“宗敏啊,你知道大顺现在有多难吗?”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深沉与无奈,仿佛是在诉说着一个无法言说的秘密。
景常浩抬头看了看自成,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大顺的难处,他哪能不知道?说到底,还不是一个“钱”字闹的。他的心中充满了无奈与苦涩,仿佛是一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
自从林小风那年开始,顺军就到处打仗,没个安稳的地方落脚。抢来的钱除了养兵就是买马、买兵器、做盔甲、买粮食。好不容易在西安定了都,又占了山西、陕西两省,地方大了开销也跟着大了。俸禄、军饷、修城墙、买武器,哪哪儿都要钱。更别提那些投降过来的明军了,要是停了他们的俸禄,他们铁定又跑回明廷去了。他的心中充满了对现实的无奈与对未来的担忧,仿佛是一个站在悬崖边的人,随时都可能坠入无尽的深渊。
自成一心想着钱,可大顺又没多少税收来源,商税也收不了多少,只能靠抢来维持朝廷运转。北京那一仗败了后,他还想抢赵周二王的钱来应急呢,结果又被黄得功给搅和了。他的心中充满了愤怒与不甘,仿佛是一个被命运捉弄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困境。
景常浩心里明白大顺和自成的难处,但对孔府还是心存敬畏。他再次劝道:“皇上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大顺可就麻烦大了!所以……”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恳求与无奈,仿佛是在为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而惋惜。
“所以朕才把你们叫来商量对策嘛!”自成打断了他的话,示意大家坐下。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与决心,仿佛是一个即将做出重大决定的君主。
坐下后,自成继续说道:“衍圣公嘛,就是给皇帝写投降书的。不管哪个朝代更替了,孔府都能稳如泰山。等将来天下都是咱们大顺的了,衍圣公自然也会向朕投降,成为朕的子民。朕从自己的子民那里借点钱花花,有错吗?”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理直气壮与不容置疑,仿佛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的解释。
自成这么一说,景常浩心里的疑虑就消了大半。他想着,衍圣公说白了也就是个工具人嘛!他的心中充满了对现实的无奈与对未来的迷茫,仿佛是一个被命运摆布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宿命的束缚。
他低头想了想,自成又补充道:“这事儿有三个难点:第一,士兵得扮得像建奴;第二,行动要快,最好一天之内搞定;第三,得让明廷和老百姓都相信这是建奴干的,跟咱们大顺没关系。”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冷静与决绝,仿佛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战斗而做准备。
君臣四人商量到半夜才定下了这个计划。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与对现实的无奈,仿佛是一群在黑暗中摸索的人,试图找到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
第二天一大早,两个明军俘虏就被顺军带出城去。城外一顿毒打后把他们绑在马背上往魏县方向押送。路上正好遇到了明军的探子。双方对峙了一会儿后顺军的士兵勒住马对俘虏说:“我交代你们的话都记住了吗?”他们的声音中带着一种威严与冷酷,仿佛是在对待两个无关紧要的棋子。
“记住了。”俘虏回答道,他们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与无奈,仿佛是在面对一个无法抗拒的命运。